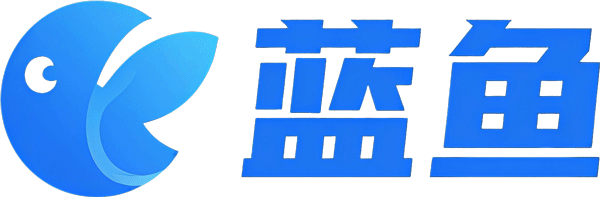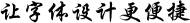你明白吗?身边同伴会促使你再度思考平素看待的劳作与生存。我有个朋友阿斌,他最近半年的际遇,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这篇文章,会详尽讲述一个字体设计者怎样从困惑变得执着,再次领悟到“匠人精神”的历程。倘若你也在创作领域经历过迷茫,他的故事也许能为你提供些切实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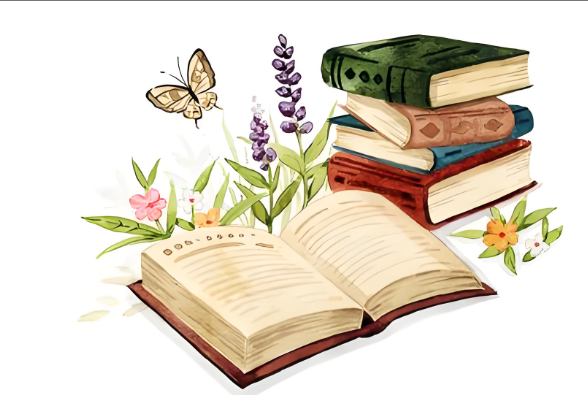
阿斌是我在美术学院时的同窗,工作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了字体设计领域,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摸爬滚打了八个年头。圈内人都知道他技术不错,参与过很多商业上的设计任务。不过差不多从去年起,我明显察觉到他状态不太对。过去谈论字体时,他总是充满热情,能详细地讲上大半天某个字体的由来和特点;可那阵子,他嘴里净是提“项目时间”、“客户资金”、“当前设计潮流”。他说,那不过是按部就班地干活,看谁完成得更快,谁更会迎合客户罢了。他对字体的喜爱,好像已经消失了。他写的字,虽然技巧上没毛病,但总让人觉得缺少点什么,业内私下里说,就是“匠气”太重,“匠心”不够。
一个重要的变化出现在今年三月上旬。一位他十分器重的老前辈,单独约他谈心,非常坦率地批评他最近创作的字体风格过于激烈,为了取悦市场而牺牲了字体应有的平和与雅致。这番话像一根刺,深深刺痛了阿斌的心。他醒悟到,自己正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可能沦为一个技艺精湛的“字体匠人”,而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字体艺术家”。他感到那种没完没了的让步和加班实在令人疲惫,因此他决定要采取行动来改变现状。他向我表示,他想要歇一歇,只为自己,纯粹为了“字”本身,做些事情。
四月的京城,柳絮漫天飘扬。阿斌做出了一个显得有些固执的选择,他谢绝了接下来两个月里所有可以推掉的生意,独自待在工作室,专心致志地学习临摹古代碑帖。他从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开始,每天坚持练习四个钟头。这并非机械地照搬,而是用心去理解碑帖的笔法,他形容这是在跟古人交流。他仔细研究每个字的构造、笔画的来龙去脉,体会一千多年前那位书法家挥毫时的韵律和力度。这个过程非常单调,进步很慢,偶尔一整天都感觉一无所获。然而很奇妙,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磨炼里,他发觉自己那颗被商业计划搅得心烦意乱的头脑,渐渐变得安稳了。
学习不是终点,而是途径。阿斌的意图是设计一套带有“匠人精神”的宋体字。他向我说明,真正的匠人精神表现在每一个细小之处。比如,一个基础的横画,他会探究古代木活字制作的刀工,使笔画收尾不是突兀的直角,而是带有轻微手工制作的圆滑曲线,这样能让文字在电子设备上呈现时,轮廓更柔和,观看更惬意。比如,他常常为一个笔画转角的装饰细节,不断修改数十回,力求达到“略微多一点就显得臃肿,稍微少一点就显单薄”的恰当状态。这种对细微之处的严格把控,在注重效率的商业合作中很难做到,却正是字体艺术魅力的核心所在。
你或许会觉得,这听起来过于守旧、过于耗费光阴。然而阿斌的方法并非完全摒弃当代技术。实际上,他巧妙借助现代手段来辅助他的“匠人精神”。他借助精密扫描设备将临摹的笔画转化为数字形式,在应用程序中进行精准的丈量和对照,研究黄金分割的数值。他还运用附加模块来统一检测文字的视觉均勻性,从而显著减少了人工复核的复杂过程。他提到,科技使人的双手得以解脱,使人可以更加专心致志于那些需要个人品味和审度的关键性创造活动。工匠精神并非意味着要退回到手工制作的环境中,而是要善于运用当代的先进设备,以更加迅速和准确的方式去实现所谓的“完美”。
这个阶段,比他预料的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也更为不易。到了六月尾,他的字库里,才刚集齐一百个不到的常用字。这期间,他反复经历着内心的动摇,还有多次从零开始的挫败。某个时段,他觉得字体的风格不妥,显得过于局促,便又重新临摹颜真卿的楷书,学习那份雄浑大气的神韵。他风趣地说:“这真像是一场修炼,磨练的并非技艺,而是耐力和心态。”他给自己定下的计划是,今年岁末之前,要编撰出一种集六千余字于一体的字集,他清楚这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然而他仍旧甘愿为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企图,倾注全部心力。
七月份,阿斌无意间把部分做好的字体样稿分享给了几位业内经验丰富的设计师看,结果得到了他们非常高的评价。有位前辈表示,从这些字里感受到了“岁月的沉淀”。更让阿斌没想到的是,一家很在意品牌形象的大公司主动找上门,想买下这套字体的首批商业使用权,准备用它来更新自家高端产品的品牌标识。他相中的,是这种字体所蕴含的“独具匠心”的韵味,那远非那些工业化批量生成的字型可比。这件事让阿斌愈发认定,在急功近利的环境里,那些经过精心雕琢、真正具备“匠人风范”的造物,自会拥有非凡的意义和持久的活力。
阿斌现在还在他的工作室里,每天和笔墨以及像素打交道。他的经历让我懂得,“工匠精神”在字体设计领域,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它体现为对每一笔画的尊重,是对于漫长创作过程的坚持,是在商业浪潮里守护内心那份对“好”的纯粹向往。它让原本单调的字符,变得富有温度和内涵。
希望阿斌的经历能引起你的共鸣。你是否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追求过那种执着专注的态度呢?